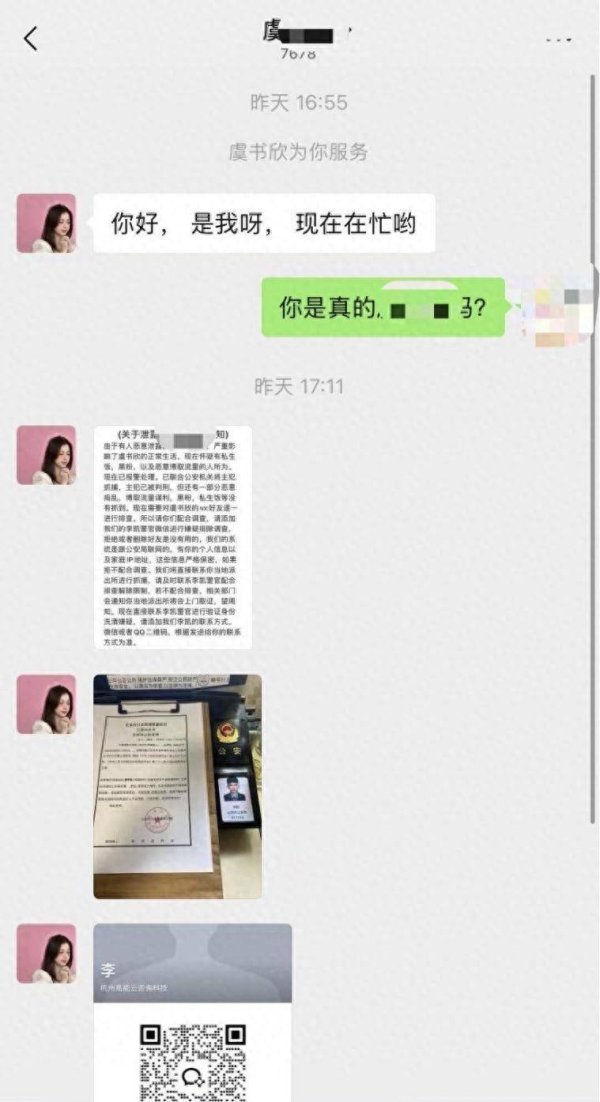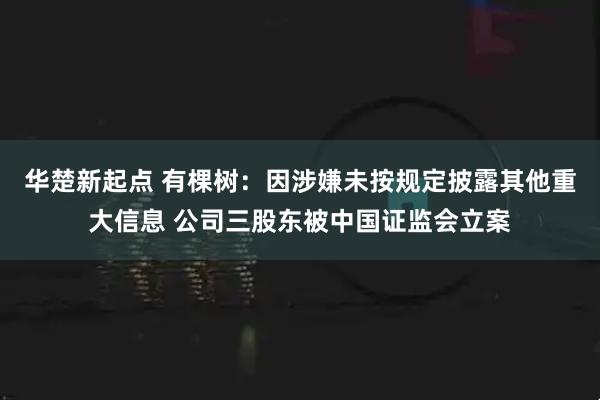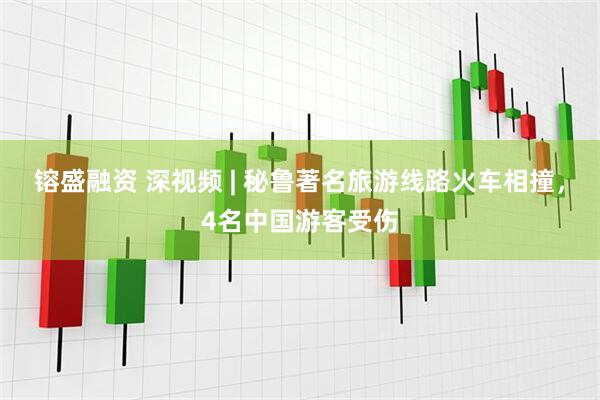摘录:《中国士文化的道义哲学研究》创高网
士文化的道义哲学内涵
“道”是推动宇宙运行最根本的规律,是中国乃至东方古代哲学的重要哲学范畴,表示“终极真理”。“义”是指公正合宜的道理。“道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本身是用来维系和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准则。道义者,道德和正义也,要求遵守诺言、履行盟约,注重个人的功修和道德修养,在逆境中不断砥砺自己的情操。道义是对敬畏和忠诚的最好诠释。道义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是一种人文关怀,是一种对他人负责的高尚境界,是发自心底的一种社会责任。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被公认为是“重义轻利”的道义论。在中国儒家、道家、佛家三家构成传统文化三位一体的基本框架,是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思想要素。深受儒家、道家、佛家思想影响的传统道德意识,强调“重义轻利”,以“义”节“欲”,以“义”制“欲”;强调以仁为本,以义为行。君子取义必忠贞,遗世独立;小人贪财必无信,世人不耻。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士”具有“道义”精神,以道为尊,以义为人生导向,这是士人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易·系辞上》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史记·太史公自序》:“《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道义即是法律的内涵和外延。道义作为“士”而言,体现的是对“道”的坚守与担当,代表了社会正义和良知。孔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道义要求人们在处理相互关系,采取有效行动之前,把对他人以至于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放在首位,宁愿自己吃亏受苦,也不损害他人殃及无辜,这种慷慨相助的高尚情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骄傲,这种同情与怜悯,是一个群体或国家在危难中得以生存的重要保障。士人立身之大节,如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士族有很强的荣誉感和道德感,重名节、人格与尊严,并将之上升至重于生命的高度。《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子。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具有重要的文明进步意义。
展开剩余92%古人说:“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有道德之称”。
“士”以学和道德修养为己任,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以出仕作为自己的前途,仕则忠于职守。王子垫问孟子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又说: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孟子的“义”其实已经不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而与墨子的“兼爱”思想趋于相同。荀子对“士”的要求重在遵从礼义,认为士的天职是正身,“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荀子·王霸篇第十一》又曰:“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其他诸子都把士与道义紧密连结在一起。士掌握着中华文明道义的至高点,以修身守德为根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追求目标。义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范畴,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管子倡导“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环绕“义”的概念作了交集。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朱熹指出:“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儒家之义强调主体性和实践性,使义既内敛为行为主体的品格,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播种下道德文明的基因,又外化为主体行为的品格。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们具有敢于社会担当的个人品格,以及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道义精神,但其时含义与现代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崇尚的传统美德,而“忠”居于首位。历史上有关“忠诚”的事迹数千年来一直被人们不断传颂。“义”是儒家思想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其在“义”不能被统治者所用的时候,就衍生出了“忠”。不过在封建社会中,忠诚愈往后演变,愈有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味道,但“忠”,依然是值得所有中国人去好好体会和学习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以道义为己任是先秦士族共有的精神特点。先秦士族在面对道义或尊严无法解脱难以处理的局面,往往舍生取义,以死殉道。“君忧臣辱,君辱臣死”,卫国大夫弘演用生命殉主来演义忠诚。齐景公时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因分桃引发争功,最后全都惭愧自杀。“二桃杀三士”,士为了道义毫不苟活。孟尝君的一个门客怀疑孟尝君与门客“所食不同”,“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这个人见孟尝君的饭菜与自己的并无两样,非常羞惭,觉得自己心胸狭窄,不配称士,乃拔剑“自刭”而亡。士就是如此有羞耻之心,且勇于承担,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从另一方面展示的君子的个人品行,是自发的“忠”的行为,这与后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强迫之“忠”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中,“崖山海战”兵败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宋朝覆亡,崖山海战10万军民投海殉难,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丞相陆秀夫背负幼帝赴海而死,这个民族表现出何等的宁死不降精神,保持了崇高的民族忠义和气节,何其壮哉。此战之后,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诸子百家繁盛的学术氛围,有着不一样的学术和道德信仰,士族的精神以及他们的人生追求上也呈现着缤纷繁杂、千姿百态的图景。但无论信仰是多么复杂,无论是道家、墨家、儒家等,都无不显现出先秦士族以道义为己任的精神和高扬的理想主义。孔子在建立儒家精神体系之初,便对先秦士族群体指出了一条士族立身垂范的行为准则,要求士族应该把对道义的追求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追求。墨家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国不相攻,家不相篡,人不相欺的社会秩序的伦理,它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其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面对混乱社会现实,墨子遵守道义,反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着的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吞并,人与人之间的相厮杀劫掠。道家所积极倡导的无为、贵生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世人的深切关怀,他们提倡君王应无为而治,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在先秦时期是一种正面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因为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所造成的生灵涂炭、民生凋敝已经伤害到这个社会的良性循环。道家所主张的思想和倡导的精神,也是一种对生命个体的道义担当。孔子的“仁”主要是伦理学范畴,“仁”不是单一的道德,而是以忠孝为本、包罗众德的道德。“仁”是孔子追求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孔子的修养理论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强调“为人由己”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且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德原则。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征战频繁,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和沉重灾难,诸子百家都力从自己的政治主张出发,对“无序”的社会提出了“救世”方案。“人道”精神是春秋战国时代学士们著书立说的重要主题,孔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仁”;墨家讲贵义、兼爱、非攻,主张互爱互利,公平正义,反对侵略战争。墨子“止楚攻宋”,体现了墨子“兼爱、非攻”思想和实践精神。《孟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抨击当政者为了占有更多的土地,不顾百姓疾苦,使成千上万的百姓丧失性命。《孟子·公孙丑下》:“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墨学思想乃中华民族精神延绵不绝的重要思想源头之一,传承千年激励着无数代仁人志士为真理和理想而努力,至今仍闪烁着不朽的光辉。墨子提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其中观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彰显其民本思想。另外,如其“兼爱”“非攻”等反战思想;政治上的民主意识、平等思想;崇尚法仪的法治思想;亲士尚贤的人才思想;劝人为学的教育思想;开拓创新的人文科学思想等等,对于当代世界和平、政治文明、依法治国、经济发展、道德建设等都极具借鉴价值和积极意义。
阐述道义最为系统和精辟的是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指出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义”。士人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看重名誉和道义的民族,为了大义舍生取义。先秦的士贵族有风骨,有精神,知廉耻,守承诺,这是对社会责任、道义担当、士族良知的阐释。各家各派在站在自己立场、不同程度上各有轻重,无不显现出以道义为己任的精神和高扬的理想主义。但是这些所侧重的道义与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状态灌注到先秦士族群体的精神意识领域的。作为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阶层,又处在这么一个反复多变的动荡期,他们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处境的确相去甚远,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就必须要找到一种心理的期许,在自己的精神王国里树立起一面理想主义的大旗。他们所树立的人生理想更是鞭策他们不断前进的目标和标杆,他们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辅佐和影响君王,推行他们所提倡的思想来实现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生、现实、社会的担当和责任。
孔子要求士族应该把对道义的追求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追求。要求他的每一分子“士”都能超越他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这也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士作为精神意义上的文明载体,道德仁心的化身,发挥着维护道义、存续文明的积极作用。士以学和道德修养为己任,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以出仕作为自己的前途,仕则忠于职。士大夫精神视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修身进德,淡泊名利,清廉自守,一心为公,品行高洁,为中国社会大众树立了高尚的人格标杆,引领社会进步。他们的精神最突出的特点,每当国难临头之际,他们都能挺身而出,舍生取义,前赴后继地流血牺牲,激励万民起而救亡图存。中华民族历尽劫难而始终没有被灭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士”的精神在发挥作用。
士君子是代表士之道德的一个重要概念。《墨子·尚同》云:“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墨子·天志上》载:“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创高网,则大相远也。”《荀子·子道》载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中,子路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回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士君子在道德上要求高于“士”。《性恶》说:“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修身》曰:“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荣辱》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孟子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士君子的正义、风骨、精神、气节、名誉等是其文化的灵魂。士君子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思想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尚操守,重然诺,抗强权,有气节,明大义,他们大都有一种超越物外的理想追求,不注重物质财富的“寡欲”,不贪图名誉利禄的“戒满”,有着高尚的人格情操和道德风范。战国是纵横策士辈出的时代,也是任侠志士施展的舞台,一部《战国策》写尽了先秦士子的叱咤风采。《荆轲刺秦王》中荆轲是墨家的代表人物,他遵循“道”,是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实践者。荆轲是一位具有侠肝义胆又充满正义感的义士,透过“刺秦王”这一壮举,表现了荆轲重义轻生,为燕国勇于牺牲的精神,展示先秦侠义志士之风流韵致,从中让人们更准确地把握先秦士文化内涵和精神。“千古墨侠名荆轲,盖聂句践识不多;士为知己身先死,击筑悲歌易水别;纵有三千壮甲士,五步之内唯有我;击而不刺为兼爱,从此天下一中国”(卢飞宏《荆轲刺秦王》)。可惜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使用了“春秋笔法”,隐没了荆轲思想的光辉。“再说荆轲刺秦王,千年悬案要商量;墨侠剑艺惊天下,智勇胆略盖无双;近来读史略有思,抑墨扬儒不应当;从来史家多如此,揕而不刺混过场”(卢飞宏《再说荆轲刺秦王》)。豫让是春秋晋国智氏的家臣,古代四大刺客之一。他为报答智伯瑶知遇之恩,坚守心中的道义,以明君臣之义,伏桥如厕、吞炭漆身多次行刺赵襄子,最后自刎而死,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人间道义、士人的气节和忠义,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千古绝唱。聂政、荆轲、豫让都是《战国策》上有名的豪侠之士,他们为了报答他人的知遇之恩,能够不惜生命、刚烈永决,为朋友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他们身上体现的古代英雄节义精神,让后世感佩仰慕。他们都是古代政治舞台上拥有自由个性、血性勇气“士”精神的代表。“忠诚至上”“以武为本”“重名轻死”,这是先秦武士道之精华,敢于以身殉道是华夏武士的永存符号。他们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追寻他们超拔豪迈、慷慨悲歌的一生,缅怀他们为了个人的名誉或国家的利益不惜以命相争的牺牲精神,祭奠他们为了人格的独立和做人的原则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风骨。中国武术士道传统和武士道精神,自秦建立中央集权制以后,武士之风逐渐衰弱,在政治上和社会中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存的土壤。
墨子以“非儒”起家,不满儒家维护强权高贵、尊尊亲亲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反对现有秩序和各种侵略战争行径,它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墨家整个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之中。墨家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目标,维护公理与道义,提倡人与人之间不分贵贱,平等互爱,“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人与人之间互争互害的“别相恶、交相贼”,倡导“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表现出的主持正义、追求和平,以及平等、侠义的思想。墨子的“救守”思想是一种匡扶正义的行为和帮助弱者生存的义举,也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思想。墨子为门徒培养出了“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英勇果敢精神,其以民为重、游侠四方、利义并重、行侠仗义、主持正义、抗暴安良的观念和文化,广为后世习武者所推崇。墨家本身就是战略级别的人才,墨子手下八百子弟,墨家曾在楚国与公输班论战,攻城之法尽为墨子所破,足见墨家的团体也是带有一种“侠义”或说是“士道”。墨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杰出代表,虽然其发展在后来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社会环境下势微,但其博爱、平等、非攻等思想,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它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独立之人格,兼爱之信仰”是墨子自信,他说“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在。”
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几乎每一次社会思潮的涌动和文化现象的繁荣,并由此推动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无不闪耀着理性主义的熠熠光辉。“士”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兼济天下”的情怀,进而发展为“修齐治平”的一整套道德理念和行为规范,重点体现出士文化的理性和道义。先秦时期的士族身上凝结着中国知知识分子阶层诸多优秀的人格品质,他们具有高尚的人生理想追求和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他们的光辉形象总是这样的耀眼夺目,他们之中有的知恩图报,有的睚眦必报,有的勇于直言进谏,有的廉洁奉公,有的坚定自己的信仰,不屈其身,不降其志,保持精神的高洁。中国知识分子自始便有着某种超世间的精神来问世间事,展现“士”的精神与文化自信,具有崇高的理想追求和人格魅力。中华文化及中国社会持久而艰难的保存和延续中,中国知识分子忍辱负重、牺牲自我,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理性在哲学上是说思维上的严密的科学性,是一种特殊的确认普遍有效的真理的方法。哲学上的非理性是指理性被歪曲了以后的一种非理性行为。“士”追求事物的本质,以理性观念和态度,用“道”来改变世界,这一精神从先秦下及清代,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人的传统之事。宋以后在儒学复兴和重整纲常的时代氛围中,宋代士大夫,特别是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为了重建人的哲学,通过对理欲、义利等方面的论述,以及行为上的自觉践履,进一步高扬和深化了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性精神。中国士大夫很多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涌现出一大批文化大家。如文学家苏轼,程朱理学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以及陆王心学等等。“阳明心学”,肇始孟子,兴于程颢,发扬于陆九渊,其理论杂糅了中国道教和佛教的思想精髓,摆脱了以往儒家只求理念不讲实践的枷锁。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思想。王阳明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在古代士人中纵横家占有重要的地位。纵横家以《鬼谷子》为代表的哲学观,深受《老子》哲学的影响,其道家思想体现在纵横“裨阖”的社会活动之中。纵横策士们在道家思想的指导下,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力求“变动阴阳”,从而达到“柔弱胜刚强”的目的。纵横家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他们在春秋战国时期,适应了兼并斗争需要,提出“合纵”或“连横”的策略。他们在已有的国力基础上,利用联合、排斥、威逼、利诱或辅之以兵之法不战而胜,或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益。汉代刘向在校刊整理《战国策》时,也高度评价了纵横家的作用与影响。他说:“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苏代、苏厉之属,生纵横长短之说,左右倾倒。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书录》)纵横家的智谋、思想、手段、策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智慧令人叹为观止。秦末汉初张良是谋士的杰出代表。秦灭韩后,他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未中。逃亡至下邳时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深明韬略,足智多谋。秦末农民战争中,聚众归刘邦,为其主要“智囊”。楚汉战争中,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结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为刘邦完成统一大业奠定坚实基础,刘邦称他能“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张良向刘邦提出的“聚集三王,方可与霸王一战”的计策,成功帮助刘邦击败了楚汉战争中最强劲的对手西楚霸王项羽。张良为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汉朝建立时封留侯,后功成身退,作为中国谋士的代表人物,文韬武略,千古流芳。
在中国古代“士”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怀,将“道”作为终生追求的目标之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之乐而乐”,这些都体现了士人、士大夫内心的精神世界,这种去担负天下兴亡的责任的文化和意识,在中国古代士人、士大夫身上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具自尊感,古有不吃嗟来之食及不为五斗米折腰者。文士爱名节,重义轻利,孔子过盗泉渴而不饮,孟子喻义不言利。武士以“重然诺,轻生死”为业道。他们尊崇“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情怀,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爱国,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士为知己者死”,“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能以身许国,毁家纾难。他们的信条是“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普遍社会属性。作为君子、作为士大夫,就应该直道而行,坚守原则,坦坦荡荡,以正道行走于天地间;真正的士大夫,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都要百折不挠,不改变心志,不助纣为虐,敢于为道“不为三斗米折腰”;敢于为道“隐身自晦,不与无道强权合作”;敢于为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中国传统文化受儒家影响很大,立道、行义与修身,培养以“仁义”为核心的乐道、诚信、忠恕、克己慎独的道义精神,是士精神和文化修养的重要内容。中国士文化在历史演变中走向了一条君子之道。《论语·述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对于“小人儒”来说,他们没有道义的追求,没有正义的立场,没有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精神和人文关怀,他们对弱势群体也没有同情心。还有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学者”,他们把自己绑在利益集团的战车上,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毫无廉耻,为了一根“骨头”,他们就会出卖自己的良知和灵魂。两千多年前孔子对他弟子的谆谆告诫,最忧虑的就是读书人的人格分裂,知识分子的道德败坏,但直到今天“小人儒”仍然层出不穷,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人格有一个发展与变化的历史过程,但其整体趋势是逐步扭曲和下滑。科举从隋唐到清代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封建王朝,《儒林外史》写“士”在科举制度驱使下,八股士、假名士们灵魂被腐蚀,人格遭扭曲,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描写了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昭示了封建末世无可药救的衰落。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提倡的“仁义”,“礼乐”,“德治教化”,影响了中国及周边国家近两千年,至今仍然在一些国家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儒学之道是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圣人之学”,重视“私德”的教化作用,能够有效地促进人格完善,维护社会稳定和协调人际关系,有利于培养进取精神,对古代“士”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影响很大。而在社会的文明进程中,文明的精神是由群体决定的,提高群体的德智水平是关键。群体提升公德,公智需要智慧,开智与修德要同时兼备。“私德”是指有关个人内心修养的范畴,公德是指社会公众生活中关于廉耻、公正、勇敢等规范。私德虽然对于集体进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政治约束力所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孔孟之学在社会教化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儒家文化在治世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在社会文明发展中,如果将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个人关系道德和伦理代入到国家政治关系之中,那将是对社会发展带来具有巨大的危害性,我们要从2000多年封建专制历史发展中吸取教训和得到启示。
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士大夫文人在体制与个性的心理冲突中提供了调和自适的思想基础。在人格上,形成“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的人生境界,常怀一颗善良的心,有道德,仁厚儒雅的气质。所谓“亦官亦隐”的弹性心理结构,就是儒释道多元互补的稳定的文化结构。隐逸文化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处世方法的一种态度,是文人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体现,是中国文明史上贯穿始终的一个文化现象。道、儒思想中所蕴涵的隐逸因素直接促成了后世隐逸思想的形成,在佛教趋于中国化的过程中,其天然的出世态度,以及心性理念的发展,也对中国古代文人的隐逸思想发生了综合作用,儒释道三者共同构成了隐逸思想的基础。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隐士出现,而关于隐逸的思想,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是道家与儒家思想作用的结果。秦汉之间的“方士”传统,促进了隐逸文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战乱与分裂不断,政权更迭频繁,以及玄学的兴起,使隐逸之风达到了历朝历代的顶峰,大量士人选择辞官归隐,隐于竹林山间仿佛成为了当时士人间的社会潮流。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不仅是一个积极入仕的形象,同时,很多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向往自然,归田园居的梦想。在这样一种隐逸文化中常常呈现出的是率性自然,“穷则独善其身”,修身的内在倾向,“不求闻达于诸侯”,就是隐居终南山,这样一个隐士的偏好和意愿。陶渊明的诗形象的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的隐逸文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应该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士大夫内心经历了政治波折之后的心境,一种恬淡虚无的境界。在这样一种隐逸的文化中,强调的是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与隐者同的这样一种文化,在对待得失、对待名利中有一种恬淡与豁达。但历史上的隐士之风,对后世文化也起到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士大夫面对现实问题时缺乏担当和以及逃避的思想。
士大夫精神传统一直贯穿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创造、延续和发展,对当时社会秩序的建设,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这种精神传统在近现代历史上受到冲击,但仍然体现在许多优秀的现代社会精英身上。文化传统具有强大生命力,作为中国当代的精英阶层,理应继承这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士”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的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士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升华的瑰宝创高网,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粮食,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没有传统就没有文化,文化的传承性昭示我们有必须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士文化。随着科举制度在清末的没落,伴随着“士”的阶级也就走到了尽头。他们的存在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也是创造者,他们为中华历史长河中谱写千年来的旋律在近代也慢慢消声,现代人所追寻只是“士”的表面“印迹”和影子,真正“士”的思想和精神早已离我们远去。我们要尊敬“士”这一族,因为他们的气节与对历史所作出的贡献,但我们也要反省这一族,因为他们的得失与堕落。
古代“士”要求文武兼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士”除了有文化外,还要会武艺,有专业技能,有深厚的“六艺”教育根基。《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武士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文化是“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武士,就有“武士道”。后来中世纪日本的武士道,便是基本沿承了中国春秋战国的“士之崇奉”。日本武士道凝聚了中国儒家“勇、仁、礼、忠”思想,以及佛教文化等,汲取了其本土的神道教意蕴,而变为日本国民的普遍道德信仰。中国武士道与日本武士道在文化上、思想上和精神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作为各自民族尚武精神的代表,他们都在各自发展中对本民族文化和性格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武术道“歪曲”了中国武士道的思想和精神,走向狭隘化和极端化。中国武士精神是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武术中“道”精神的凝练与升华,其精髓是中国“武士道”,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生存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我们要重视中国武士制度的重建与复兴,促进中华武术国学的发展,让每一位习武者将成为一名“中华武士”作为崇高的荣誉和信仰。武术乃止戈之术,大道之学,继先人武德武风武魂,传中华武术之大道。武是侠的立身之本,侠是武的人格升华。《墨子·经上》:“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史记》之《游侠列传》,司马迁赞扬了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武侠精神深受墨家精神影响,体现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具有诚信守义重承诺,匡扶正义,见义勇为,舍生取义,不居功自傲,救危扶困,不恃强凌弱等中华民族优良品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手之妙者,改天换地”。先秦的侠义精神和文化焕发着社会正义感的思想光辉,它已深深的融入中华民族的生命和文化“基因”之中。“侠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有着许多道德上的优势。这种文化追求人的精神品德,重义轻生,敢于对抗强暴,有着自己的一套道德体系。虽然在当今法制社会一切行为以法律为准绳,不提倡个人凌驾法律之上,但是侠文化中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追求公平的世界观和不畏强权的价值观,以及侠客文化背后的“士”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华夏之贵族,自汉而亡。先秦贵族精神“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汉唐之后,贵族的流风余韵,早已烟消云散。中华民族精神,古代先秦与汉唐及其之后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形态,后者失去了前者的风骨与精神。华夏之兴在于墨儒释道法之融和。道儒墨法合一,共同体现中国文化的内圣外王体用一贯。厘清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实质与“儒表”之下“法道墨互补”的文化结构,有助于抓住中国传统社会真正的症结弊病所在,将儒家思想从尊儒与反儒对峙的怪圈中解放出来,理性看待儒家的思想资源,从而善加利用它对于现代社会有积极意义的一面。重新定位儒家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要重视墨家思想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于重塑民族性具有重要意义。
墨家在中国文化的总体构架中,在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形成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及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墨家学说在多元互补而又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以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与技艺而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在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了自己学派的特色。弘扬这一民族思想和精神,中国的活力和智慧将不可穷尽,中国的前程和未来将不可限量。它是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思想文化,必将指引中华民族走向充满希望的明天。“诸子显学大道扬,墨儒之争势难当;述而不作是腐儒,仁义道德千年殇;兼爱非攻行大义,节用则兴佚则亡;尚贤任能政清明,兴利除害万世昌”(卢飞宏《读墨子有感》一)。
墨家是华夏真正贵族文化,它的思想是华夏贵族思想的理论源泉。墨子的思想在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时代意义,当今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战略,正是墨子“非攻”思想的重要体现。它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我们每个人应对社会、人生中的诸多问题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与借鉴意义。墨子及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与重视。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在中国“和合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公元2020年5月8日,庚子年,农历四月十六)
作者简介:卢飞宏创高网,原名卢绪波,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非遗武术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当代武术名家,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吉林省武术科普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等约300余万字的武学巨著。
发布于:山东省扬帆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